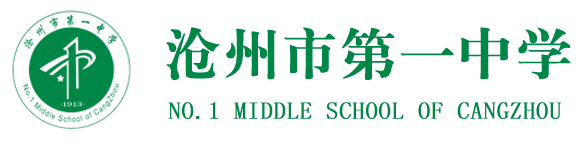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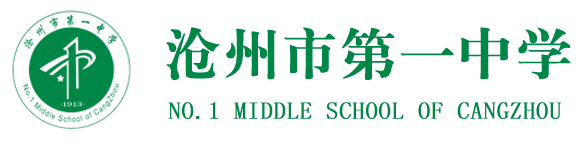
第一次听说“沧州一中”这个辉煌的名字,在小学二年级,那是1980年,村里的小学专门为考入一中的校友尹海英开大会发奖状,我当时坐在前排的小板凳上,盯着这位大姐姐,羡慕死啦!
三年后,我的堂哥孙振强也考入了这所学校(高中),他成了我最亲近最直接的表率!
1984年夏天,我以半分的优势考入梦寐以求的沧州市第一中学。当年我们乡的录取线是233.5分,我考了234,另一位最要好的同学,也是我的堂叔孙文明以半分之差,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上了一中。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人生的不平和无奈!
进入一中的第一天,我看到了如今已被一中禁止,而在其他学校尚在流行的考生分班排行榜。我被分在四班,在榜上我是倒数第二!看到这个榜,多少有些心灰意冷,没有太多上进的劲头儿,也就是凭着小学良好的学习习惯,没堕落罢了!
结果到了期中,“吊儿郎当”的我居然考了一个13名!
咦——有门!
我想,再加把劲,看看会怎么样?于是,开始努力。
期末成绩下来了,第五名!
从此,我树立起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自信。
与此同时,另外一种自信,也正在被语文老师任进军老师树立着!
任老师上课有个老习惯,就是按座位的前后顺序,让同学们分段朗读课文,而她头也不抬一下,看着自己的书本。
轮来轮去,轮到我了。那天读的课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是一篇很绕嘴的题目——《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正是为此,我一直对格鲁吉亚这个前苏联的小加盟共和国很有好感,因为第比利斯是她的首都。直到2008年8月8日,它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给全中国人民添腻歪,我才一改初衷。
轮到我读了,我却没有任何动作。
任老师低着头问:“下边该谁了?”
我站起来回答:“我!”
“怎么不读?”
“我读不出来?”
听到这话,任老师才抬起头,用她特有的高傲而又犀利的眼神盯了我一会儿,责问到:“你又不是哑巴,为什么读不出来?”
我还没有回答,全班同学们早就按捺不住,来了个集体作答——“他是个磕巴嘴……”然后是哄堂大笑。
尽管我把头低得不能再低,但依旧没能阻止泪水流下来,一滴一滴地滴到书页上。
好一会儿,我听见任老师用温柔而又不容抗拒的语调说:“我给你起个头,你能读吗?”
“能……能读……”我哽咽着。
“那好!”
……
从那之后,任老师改变了她保持多年的习惯,每上我们班的课,不再按座位顺序轮读课文,而是由我第一个来读,而且前几次都是她亲自给我起的头儿。
半年下来,我的磕巴嘴居然好了大半,不仅如此,包括朗读水平在内的语文成绩也进步神速,很快成了语文的尖子生!
快毕业了,当时的我不知道怎么感恩,就来到学校北边的教师平房宿舍,第一次敲开任老师家的门,恭恭敬敬给她磕了三个头!
……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任老师。
今天能够向她老人家汇报的是,我这个当年的磕巴嘴,虽然没出息,只上了一个小中专儿,但刚一考入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就被刚刚从北师大毕业的语文老师看中,当上了语文课代表,几天后就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第二年就当上了社长,带着二百多号人马,在文学园地里栽花弄草折腾欢了……
2000年,加入沧州市诗词学会;2002年,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同年任沧县纪晓岚研究会顾问;同年被聘为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2004年,任沧州纪晓岚研究会副会长,《纪晓岚》杂志责任编辑;2007年,加入由沧州市政协组织的沧州市文史研究会。
业余喜读书考据,曾参与点校整理《纪晓岚全集》《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等。致力于纪晓岚研究,出版有《大才子纪晓岚》(与孙广权先生合著),另著有《沧州枣话》《乡谣偶记》《纪晓岚砚铭详注》《纪晓岚联语辑证》《纪晓岚侧影》等。(编辑 常树青)
• 我校校友回母校交流2010-06-10 14:06
• 我校07届毕业生回母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2009-02-20 16:26
• 我校著名校友李涵回访母校2008-10-29 08:05
• 我校五七届高三班毕业生聚会母校2007-09-16 09:08
• 汤韵、王纯等一中优秀学子回母校作报告2007-08-10 14:25

关注一中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