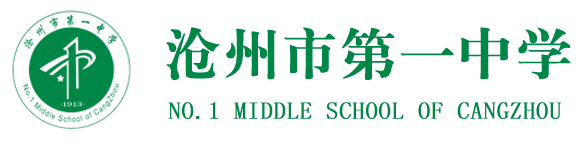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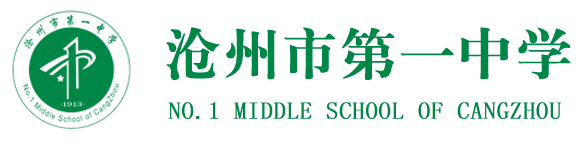
人不能无师,且“圣人无常师’’。如韩文公所言:“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在我退休前后,带我进入书画之门的李大中、陈树潮先生,授我以诗词格律的王永乐、白焕宗、申志辉先生,推我拙文见报的陈芳女士等,都是我尊敬的老师。凡师,皆有教于我,有恩于我。由此想到我的恩师李延年先生,其不仅是我的授业恩师,且当我站在能否考学升学的十字路口时,曾苦心孤诣地为我解惑,并鼎力助我完成大学学业。为避对师不尊,本文仅以先生称之。
我是1962年毕业于沧州一中的。从高二起,先生开始教我们俄语。那时,他刚从天津师大毕业,年龄仅比我大7岁。师生年龄相若,且他生性平易、坦诚、真爱博施,同学们都爱接近他。那时,“三年自然灾害’’还没过去,我们有时会把从农村老家带来的山芋干等分一点给先生,先生也会把他从北京带回的糖菜之类分给我们,彼此吃得香甜,都很珍惜。
先生精俄语、爱体育、善教学,同学们虽都是初学俄语,但都学得很好。记得高考有不少同学俄语得了满分,先生就责怪我只考了9 3分。后来我想,如果当时俄语成绩计入高考分数,大概我便不会第一个退场,也可能会考满分的,并因此一直后悔没给老师争气。但一中为我奠定了良好的外语基础,进入大学后,我很快被选入俄语高级班,假如不是“停课闹革命’’,肯定已首批选学第二外语。先生既教学又教学法,其在课堂上传授的“睡前忆讲”强记法,使我逐渐养成了 “入静一一默忆一一理悟一一强记’’的学习习惯,对我此后的学习和工作大有助益,至今不弃。先生深知“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故鼓励并帮助我们与苏联小朋友通信,以培养我们学习外语的兴趣,我就曾与苏联小朋友通过两封信。不想这竟成了先生此后受冲击、挨批判的“罪状’’,那信也就不敢留。
接触多了,便无话不谈。先生是北京人,祖父曾任武官却以书礼传家,其兄弟姊妹中,司职部队、教育、科研的都有,但与我们这些农村学生的家庭落差,并没妨碍其对我们困难的理解和同情。高考前夕,我家突有电报来,说“父病重’’,让我“速回收麦’’。我姊妹多,大姐二姐已经出嫁,弟妹年纪尚小。回家看到,妈妈有病躺在炕上,父亲正闹疟疾,在生产队分给各家的自留地里,只有我家那矮而稀疏的麦子还孤零零地立着。于是,我一面借钱给父亲治病,一面抢收,抢晒,然后人推石磨磨麦成粉,刚好救了举家断炊之急。此后父母才告诉我,之所以发电报让我回家,就是怕我考大学,因此,不让返校,不让和学校联系。我无话可说。没有劳动力,挣不够工分,分不到粮食,更分不到钱。一家人连吃饭都难,还拿什么供一个大学生呢?在姊弟中我已排行头大,责无旁贷应该撑起这个家了。我理解父母作出这一决策的艰难、痛苦和无奈。但我心犹不甘,却无计可施。为安慰父母,我乖乖地到生产队报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村支书听说我不考大学了,连大队会计的位置都给我安排好了。
十天后,父亲忽然收到先生的来信,那是一封写满两页信纸的信。先生通知我,考前总复习已开始,并责令我不管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即回校再说。捧着老师的信,我落泪了。父亲得知信是先生写来的,也很激动,我乘机以
取毕业证、等户口、拿铺盖为由,请求返校,父母同意了。临行一再嘱咐我,一定要好好谢谢先生,好好向先生解释为什么我不能考大学。
回校后,班主任狠狠批评了我,我惟诺诺,不敢强辩。先生则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并让我什么都不要想,安心复习、从容高考,一切待考后再说。
考完,我立即卷铺盖回家。如同没有高考一样,我开始正式加入生产队劳动,每日所得工分竟也长了一分。某日中午劳动归来,父亲突然举着一封信很生气地骂我,骂了很多话。我全然不顾,赶紧打开信,竟是四页信纸。先生祝贺我已被北京铁道学院(现北京交通大学)电信系录取,其余内容则几乎是写给我父母的。信中,先生讲到:高考这条路很窄,被录取实在不易;站在未来一个铁道信号工程师对国家贡献的角度,国家不希望弃学;即使从家庭利益看,即使我不上大学,也只能救急,并不能彻底改变家庭的困难状况;上了大学,国家会给助学金,能保证一个困难生的基本生活。先生还表态,会从经济上尽力帮助我。然而这件事在我家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让不让我继续上学的问题上一家人犹豫着、争论着、争吵着,父亲拿着先生的信翻来覆去地看,并不停地摇头叹息,毕竟我是全村乃至全乡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啊。最后不得不把大姐二姐等亲戚找来商量,才做出让我完成学业的决定。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先回一中取入学资料,再顺路赴京。至今我还记得先生看到我准备入学时的那种安慰和庆幸。当时我正发高烧,先生就让我在他的床上休息,为我盖被子,喂我吃药。送我去京前,先生为我详细地画了一张从北京车站到学院的路线图,还把他家的位置以及从学校到他家的路径也标注在图上。先生告诉我,他已经给家写信,父母和大哥都表示会好好接待我。在校的几年里,先生的这个家不仅从经济上帮助我,更给了我诸多温暖。先生的父母称我是他们的小儿子,先生的大哥也就成了我的大哥。先生常对他人说:“我们是师生、兄弟兼朋友”。
大学毕业后,我到天津铁路电务段工作,无论多忙也不敢忘先生,调回沧州,则接触更多。三年前先生古稀.大寿,先后有近百学生为之祝贺,足见先生口碑之好。我则用红宣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并题一诗是,“故校已难寻旧痕,天涯何敢忘师恩。多情无奈韶光逝,但愧未成鸣世人”。算是祝寿,也算对自己事业上无大建树,以至有负师教师恩的愧叹。每年,我们两个大家庭(包括儿女、亲家)都要聚会一两次,兼叙天伦。有恩师如斯,幸何如之!
先生今年已七十三岁,身无顽疾,且龙行虎步,精神矍铄,还能受邀参加市县中学的体育教学检查等活动。馨德载寿,愿先生身心康泰!
• 献给九十五岁的母校2008-04-25 06:46
• 春风杨柳万千条——献给母校九十五岁华诞2008-03-12 15:51
• 《学生参与——转型时期高校管理的视界》评介2008-01-03 12:20
• 浸在豆汁儿里的日子——有味道的大一2007-10-11 12:06
• 王纯《特洛伊战争》教学设计2007-08-08 08:48
• 校友采风---书法2007-07-26 10:39

关注一中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