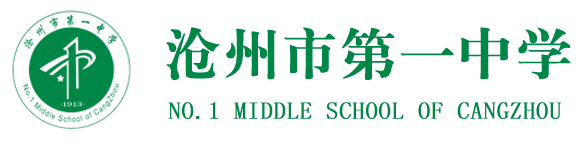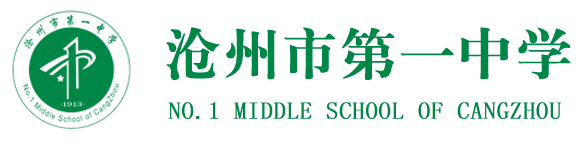钟书先生年表
1910年(宣统二年)出生
11月21日(农历庚戌年10月20日),钱锺书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伯父钱基成,父亲钱基博(子泉),叔爷钱基厚(孙卿)。
1911年(宣统三年)一岁
钱锺书出生那天,曾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为他取名 “仰先”,取“仰慕先哲”之义,字“哲良”。至此周岁抓周,抓了一本 书,父亲为他正式取名“锺书”。
1916年六岁
在亲戚家的附塾附学,曾念《毛诗》。以后由伯父教他读书。读了《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以及《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小说。
1920年十岁
入无锡东林小学。父亲为钱锺书改字“默存”,有要他少说话的意思。
1923年十三岁
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大量阅读《小说世界》、《红玫 瑰》、《紫罗兰》等刊物。
1925年十五岁
返家度暑假,乃得知《古文辞类》、《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 等大型选本,从此开始系统阅读,是一生治学之始。
1929年十九岁
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报考时,数学成绩不及格,因中英文成绩特优,被破格录取。
1929—1933年十九———二十三岁
在大学期间,建立了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观念,知识结构正式形成。 因出众的才华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人的欣赏,被看作特殊的学生。1932年,结识杨绛。1933年,与杨绛订婚。
1933—1935年二十三———二十五岁
在上海光华大学任外文系讲师。
1935年二十五岁
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 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结婚,同船赴英。
1937年二十七岁
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毕业,获得副博士(B.Litt)学位。同年,入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女儿钱瑗出生。
1938年二十八岁
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Ⅱ)回国。
1939年二十九岁
夏,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开始写作《谈艺录》。
秋,赴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
1939—1941年二十九——三十一岁
在湘西两年。其间于1940年暑假曾回家探亲,因道路不通,半途折回。完成《谈艺录》最初部分,约相当于《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完成《围城》 的布局、构思。有《中书君近诗》一册(非卖品)。有论文《中国诗和中国画》(1940)。此文后来收入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旧文四篇》(1979)和《七缀集》(1985)。
1941年三十一岁
暑假由广西乘船到上海,时值珍珠港事件。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
1944—1946年三十四——三十六岁
写作《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
1946年,短篇小说集《人兽鬼》由开明书店出版。
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48年再版, 1949年三版。是“晨光文学丛书”之一。《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49年再版而止。是“开明文史丛刊”之一。
1949—1953年三十九——四十三岁
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锺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实际干的是《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定稿工作。极少发表作品,以静静读书为主。
1955年四十五岁
翻译德国海涅的《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刊载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编的《文学研究集刊》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月版)。
1955—1957年四十五——四十七岁
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
1957年因父病到湖北省亲,有《赴鄂道中》五首绝句,寄寓了对当时形势的感受。此年父亲钱基博病逝。
1958年四十八岁
《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五十年代末
成立《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袁水伯任组长,乔冠华、钱锺书、叶君健任组员。小组的工作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暂时中断。
1966年五十六岁
“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锺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锺书轻蔑领袖著作,钱锺书、杨绛用事实澄清了诬陷。
1969—1970年五十九——六十岁
1969年11月,钱锺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不久,“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1970年7月,杨绛也来干校。在“五七干”,钱锺书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得一被逼含冤自杀。
1975年六十五岁
此年前后,海外误传钱锺书的死讯,在港、台、日本等地引起了一阵悼念活动。此误传于1977年前后被澄清。《管锥编》初稿完成,此后又陆续修改。
1976年六十六岁
由钱锺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诗作《老至》寄寓了对形势的感受。
1979年六十九岁
4月至5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莱分校等,大受欢迎。《管锥编》 1—4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收有 《中国诗和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等4 篇文章。《宋诗选注》重印。
1980年七十岁
11月,赴日本访问。在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围城》重印。
1982年七十二岁
《管锥编增订》出版。本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83年七十三岁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分主持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致开幕词。《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被列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七十四岁
《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此书上半部是1979年以后发表的三篇论文:《诗可以怨》(1981)、《汉译第一首英译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1982)、《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1983);下半部从《谈艺录》补订本摘选。《谈艺录》补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5年七十五岁
《七缀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包括《旧文四篇》和《也是集》上半部的3篇文章,共7篇文章。
1989年七十九岁
《钱锺书论学文选》(六卷本)由舒展编成,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此书包含有钱锺书新补手稿约20余万字的内容。
1990年八十岁
12月,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普遍好评。
1991年八十一岁
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锺书为首批36人之一,但他谢绝拍摄。
1998年12月19日八十八岁
上午7时38分,钱锺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当晚,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给钱先生的夫人杨绛打电话,对钱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在翌日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
“我们家”只是旅途上的客栈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锺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锺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锺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锺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锺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商务出版),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嫦娥捧出桂花酒’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锺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锺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TEFL),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 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我们眼看着女儿在成长,有成就,心上得意。可是我们的“尖兵”每天超负荷地工作──据学校的评价,她的工作量是百分之二百,我觉得还不止。她为了爱护学生,无限量地加重负担。例如学生的毕业论文,她常常改了又责令重做。我常问她:“能偷点儿懒吗?能别这么认真吗?”她总摇头。我只能暗暗地在旁心疼。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锺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锺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锺书每天第一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锺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