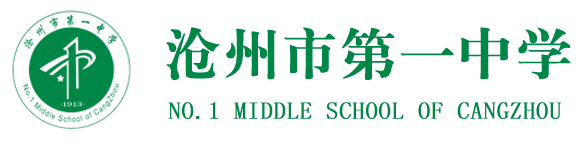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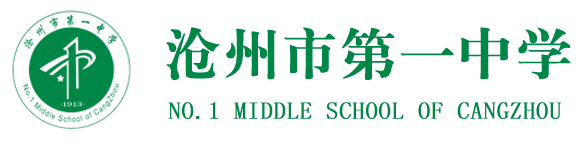
(一)巴金百年人生大事年表
1904年,1岁,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官僚地主大家族。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
1909年,6岁,在父亲李道河任所——四川广元县衙内——家塾就读,除随先生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古文观止》等传统蒙学读物外,在晚间从母亲学读《白香词谱》。
1911年,8岁,辛亥革命爆发,父亲辞官。随父母返成都,继续在家塾就读。
1914年,11岁,母亲病故,安葬于成都市郊磨盘山。母亲“爱一切人”的教诲对巴金一生影响颇大,后来称母亲为自己的“第一个先生”。
1917年,14岁,父亲病逝,大哥挑起长房生活重担,大家庭矛盾加剧。自是年起,巴金在晚间随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的香表哥学习英文。
1918年,15岁,秋季入成都青年会英文补习学校,一月后因病辍止,继续在家从香表哥学习,其间直接阅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史蒂文森的《宝岛》等英文原著。
1919年,16岁,“五四”运动爆发,新思潮涌入四川。巴金接触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等各种新刊物。
1920年,17岁,祖父病故,大家庭内部的争斗和倾轧更为加剧。读克鲁泡特金《告少年》、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中译本及《实社自由录》第一集中刊登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的文章,第一次了解到无政府主义的要义,其后称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这一年还有一件可记的事,巴金参加了成都学界反对军阀刘存厚的请愿及集体罢课活动。这是巴金第一次参与社会斗争。
1921年,18岁,参与编辑成都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以“芾甘”为署名,发表了有生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是年,参加并组织了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并发表了《均社宣言》。从此,巴金开始以“安那其主义者”自命。
1922年,19岁,七月,新诗《被虐者底哭声》(共十二首)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44期。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巴金发表的最早的文学作品。
1923年,20岁,秋季入上海南洋中学;年底赴南京入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
1926年,23岁,《五一运动史》于是年四月出版,该书是目前所见的巴金第一本单行出版的书。
1927年,24岁,一月,乘法国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二月抵巴黎,沿途写有《海行杂记》三十八则。是年,译著《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著)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这是巴金单行出版的第一本译著。
1928年,25岁,八月,完成中篇小说《灭亡》,署名“巴金”。译著托洛斯基《托尔斯泰论》,亦署名“巴金”,载于十月十八日《东方杂志》第十五卷。此文较《灭亡》早发表近三个月,是以“巴金”署名最早见于报刊的文章。
1929至1933年辗转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出版《家》、《雾》、《雨》等代表作品,译完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等。
1934年底赴日本。1935年4月6日,住处被日本警方搜查,并被带到神田区警察署拘留14个小时。同年8月,由日本回国,任上海文化生活社总编辑。
1936年10月初,巴金与鲁迅、郭沫若等21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形成。
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与茅盾编《呐喊》;后上海陷落,辗转武汉、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完成《春》、《秋》等大量作品。
1944年5月,在贵阳与相恋8年的萧珊(原名陈蕴珍,1917生,浙江宁波人)结婚。年届四十,巴金终于找到至爱。
1946年,43岁,8月到12月,《寒夜》开始在《文艺复兴》上连载。次年3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这也是巴金建国前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
(二)巴金百年人生大事年表
1949年6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文联常务委员和文协(后改为作协)常务理事。9月,在京参加政协会议,当选政协委员。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参加天安门城楼观礼。
1952年,正是“朝鲜战争”时期,赴朝鲜战场实地访问8个月,写出了大量催人泪下的文章。电影《英雄儿女》,即是根据他此时采访写下的小说《团圆》(《团圆》最后写成于1961年7月;1963年,毛峰、武兆堤将其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改编的。
1966年8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贴出攻击巴金的大字报,不久巴金即遭批判,被关进“牛棚”。
1967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巴金被点名批判。随后在上海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半。
1973年,70岁,“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宣布对巴金的处理意见:“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可以搞点翻译。”巴金埋头重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
1977年,74岁的巴金恢复写作权利,于是年五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他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
1979年,76岁,四月,巴金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抵赴巴黎访问,这是他自1928年离开法国后的第一次重访。是年底,《随想录》(第一集)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这是巴金复出后最重要的文集,主张说真话,主张对“文革”进行反思,提出了作家的“责任”问题。
1981年,78岁,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得到茅盾、叶圣陶、夏衍、冰心、丁玲、臧克家、曹禺等作家的赞成和支持,该馆筹备委员会于本年12月在北京成立,巴金、谢冰心、曹禺等九人为委员。
1991年,88岁,致信在四川举行的巴金学术研讨会,申明“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因为病……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为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
1993年,90岁,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资深作家敬慰奖”及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评委会特别奖。
1999年,96岁,二月八日,春节期间因呼吸道感染突发高热,并出现急性呼吸衰竭,送华东医院抢救成功,但因年高体弱病情反复,从此未能出院。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为被命名为“巴金星”。
2003年,11月25日,巴金的人生历程超越了一百岁的界线。
(三)巴金简介
巴金走过了一个世纪。在这变幻的100年中,他有过成功的欢欣,有过屈辱的磨难,有过痛苦的忏悔,有过平静的安宁。巴金的人生,映照着一代五四知识分子坎坷而不平凡的命运。对巴金的祝福和纪念,也是对上个世纪许多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的怀念,是对我们的民族经历的百年风雨的记忆与思索。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巴金以《家》、《春》、《秋》等一批长篇作品影响了几代青年人,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巴金在文革结束后所著的《随想录》,更是以中国第一部敢说真话的作品而著称,被誉为“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著作,标志着巴金的创作进入了巅峰。而这部作品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巴金不畏生死,率先直面自己,以无畏的勇气拷问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发出了人人想说,人人都觉得应该说但人人都没有勇气说的真实的声音,对文坛和社会的震憾,石破天惊。
巴金,原名李尧棠,祖籍浙江嘉兴,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
“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于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修学校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后经常发表论文和译文,宣传无政府主义。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该作品从1929年1月在《小说月报》以“巴金”署名连载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而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道路。1928年冬,巴金回国后寓居上海,数年间著作颇多,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1931年在《时报》上发表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首曲”——《家》,该作不仅是巴金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巴金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等地,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1940年至1945年又创作了“抗战三部曲”《火》,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短篇小说 《神》、《鬼》。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
巴金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1985年由他倡议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
届今,这位文坛老人已跃过百岁人生界线,成为古往今来、中外东西最年长、也最受人尊敬的文坛作家。
(四)少年軼事
巴金于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用他后来的话讲,他“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他的童年。
但巴金与许多出身于华贵的人不同的,他在被唤作“四少爷”的同时,却最愿意与仆人们在一起,喜欢听这些人讲他们各自的悲惨故事。
轿夫老周,即是那时巴金最常亲近的人。巴金常在马房里听他讲故事。那时在他们家的马房后,有一个轿夫们的厨房。他们做饭时,巴金就去帮他们烧火。坐在灶前的一块石头上,巴金不停地把柴放进去,结果常常把火弄灭了。这时,老周就把他拉开,用钳子往灶膛里捅几下,火又“蹭”地冒了起来。放下钳子,老周告诉巴金:“你要记住:人要忠心,火要空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次记者与巴金聊天,他很悲哀,说自己这辈子没做什么,现在又成为大家的包袱。记者安慰他,说他的那些作品,影响了几代人,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巴金却哀哀地说:“我的几百万字作品,还不及老周的八个字。”——老周的八个字,就是:“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可见,巴金不仅记住了这八个字,而且深深地把它们刻在心扉上,融化在血液中。
在富裕的环境里,小巴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他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巴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5岁那年,仁慈的母亲深深地责备了三哥,事情的起因只因为三哥打了丫头;父亲在审案时动用毒刑,经母亲劝说过后不再用刑……母亲在他幼小的心上播下了爱的种子。
母亲交给了小巴金要“爱一切人”。所以在大家庭里,巴金喜欢和“下人”们在一起。他常说:“我是在仆人、轿夫中长大的。”“在鸦片烟灯旁边,我曾帮过轿夫们烧火煮饭。在这一群没有知识、缺乏教养的人中间,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态度,我得到了那个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
“我说我不是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在巴金的心灵深处,暗暗隐藏着一种“赎罪”的心情:“老一辈的罪过,要由我们去偿还。”巴金通过《灭亡》中李静淑之口说出自己的誓言: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
(五)筆名“巴金”的來歷
巴金的本名,即学名叫李尧棠,号芾甘。此外他还有一个小名,叫升麐;他大哥的小名叫果麐,麐哥的小名叫安麐,一个兄弟的小名叫开麐,都是依“麐”字排下来的。
成年后的巴金,除“巴金”之外,还用过“壬平”、“极乐”、“佩竿”、“黑浪”等笔名。后来,巴金曾回忆说:
当时旧金山有位华侨,办了刊物《平等》,我供稿子,文章写多了,用一个名字不太好,就时常换名字,随时想起随时用,没有考虑什么用意。时间太久了,有些事一时记不起,看到文章就能回忆起来。
关于“巴金”笔名的由来,至今国内外研究者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许多人猜测这两个字来自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其实不然。巴金在八十年代接受青年学者陈思和等人采访时,曾说:
我在法国的沙多-吉里写小说《灭亡》,并没有想到拿它发表,只想自费印刷几百册送给大哥和一些熟人。我找个朋友(按:即当时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索非)帮忙。我不愿用自己的真名,想到一个在法国的留学生,不久前在昂热自杀的巴恩波,就采用了一个“巴”字,以示纪念;“金”是那个学哲学的朋友建议采用的。“巴金”不是我有意取的笔名,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灭亡》寄走后,我去巴黎,胡愈之找我为《东方杂志》翻译托洛茨基纪念托尔斯泰的文章,我在译稿(《托尔斯泰论》)上署名“巴金”。后来,这篇后署“巴金”的论文却先发表了(按:该文载于1928年10月《东方杂志》第二下五卷第十九号),最先署“巴金”的小说《灭亡》是1929年才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按:载《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期)。实际上还是《灭亡》最早用“巴金”这个笔名。
除此之外,巴金在1957年9月27日写给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也对自己的名字作了注解: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Cha–teau-Thierry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所说的“我的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巴”,显而易见指的是那位早逝的同学巴恩波;至于“金”,不难见到其实指的就是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1842~1921;Kropotkin,PiotrAlekseevich)是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地理学家和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理论家、活动家。他流寓英国约30年,潜心于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研究著述,继承并发挥P.J.蒲鲁东、M.A.巴枯宁的学说,提出一整套关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论。巴金15岁的时候,无意中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从上海寄给他的。这本书深深震撼了他的灵魂,书里面全是他想说而没法说清楚的话。那雄辩的笔调简直要把15岁的巴金的心烧化了。他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告少年》里我得到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从那开始,巴金即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终身不渝。
巴金一生写过九百多万字的文章,用过二十多个署名。但“巴金”这一名字用得最多,也最为大家所熟知。从“巴金”这一笔名的来源,不难看出巴金本人对友谊的怀恋和对信仰的坚决。
(六)巴金和無政府主義
有这样一个故事。“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从延安飞重庆,在谈判的余暇也会见了一些文化界人士。巴金就是在这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毛泽东对巴金说:“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巴金答道:“是啊,听说你从前也是。”
这个故事足以表明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信仰。也可看出无政府主义20世纪初在中国的影响。
巴金是15岁那一年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的。那时正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不久。一位不相识的朋友从上海寄给他一本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本书深深震撼了他的灵魂,书里面全是他想说而没法说清楚的话。那雄辩的笔调简直要把15岁的巴金的心烧化了。他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告少年》里我得到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从那开始,巴金即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终身不渝。
(七)真實的巴金
晚年的巴金,曾经说“长寿是一种惩罚”。他不只一次说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自己年纪太大了,对别人是负担,自己又不能工作,是一种在而不健,生存就没有意义了。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把心掏给作者,把作品拿出来跟大家交流,失去了这一切以后,他就觉得自己生存实在是没有意思,何况又确实真是很痛苦。
巴金年轻的时候,为了创作,经常熬夜。有时编刊物的朋友们逼稿,刊物又不能延期,他就常常熬夜。巴金后来说:“那时身体好,不怕熬夜。”
一般的印象中,许多作家都是随身带着一个小本,看到什么好的素材,就先抄下来。但巴金却没有这一习惯,他身边从来不带什么小笔记本,写小说之前也没有事先写提纲的习惯(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大家,例如茅盾,在写小说之前,都是要写提纲的)。
至于巴金写作时的状况,令后世感到最好玩的,是他夏天进行创作时的情景。80年代,他与姜德明在一次闲谈中曾说:
我年轻时很怕热。夏天,我喜欢打赤膊写作。光着背,只穿一条短裤。
巴金后来还回忆说:“我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写作。火车上、轮船里、小旅馆的油灯下,临时主在的朋友的家里,……什么地方都可以写。抗战期间,我随身带着一块墨,走到什么地方,找个小磁盘,倒上一点水,磨好墨就写。除了一枝笔,我是一无所有。”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马绍弥是巴金的养子,母亲罗淑在生下绍弥20天后,得产褥热病,不幸逝世了。11岁那年,父亲马宗融又在贫病中逝世。马绍弥的父亲生前是复旦大学法
小学毕业那年,马绍弥拿着学校发的履历表为难了。因为他不知道,在家庭成员、社会关系这些栏目中,该怎样填?回到家,绍弥将履历表交给巴金。巴金看了看,在家庭成员一栏中填下这行字:
李尧棠父执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职员。
写完后,巴金又关照了一句:“你以后就这样填。”
此时正是50年代初,“巴金”之名早已蜚声文坛,新中国一成立就在文化界担任要职。但是,在巴金心中,他只不过是一名编辑,一个职员。
(八)愛國的巴金
年轻时的巴金,尽管信奉过无政府主义,但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一直是巴金性格中最为突出的两部分。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巴金在国际上获得众多奖项,但在每次答词中,巴金从来都不把荣誉归为自己,而是国家。在接受法国荣誉勋章时,巴金说:“这次总统阁下光临上海,在我病中给我授勋。我认为,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成就。这是总统阁下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尊重,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的尊重,这是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象征。”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会议期间,巴金与
“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巴金经常这样说。1979年,巴金从“文革”的磨难中走出后,重访青年时代留学的巴黎。每天早晨,静静地坐在窗前椅子上,他说,他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而是上海的淮海路,北京的长安街,杭州的西子湖,成都的双眼井……他想念祖国,想念亲人。
(九)巴金談文學
巴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有人把文学的作用,一会儿说得很高,好像能治百病;一会儿又不重视,随时可以把一些作家、作品打下去。其实,文学的作用主要是长期水滴石穿,潜移默化。我文章中反复讲,说空话没有用,还是做点实际事情好;我写了几百万字,很难看出有什么实际作用。我想做些实际工作,可是又不会做。我就有了矛盾,有了痛苦。我只能写写文章,努力写真话,结果还是好像讲了空话。
巴金所坚持的,正是“水滴石穿,潜移默化”的文学观,他的“激流三部曲”是这样,《随想录》也是这样。
(十)巴金的晚年的兩個願望
巴金晚年一直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是现代文学馆,第二个是文革博物馆。
1985年巴金即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他觉得,很多的资料散失在私人手里,不能集中起来供研究者去研究,是一件很大的损失,他就希望有这么一个机构,能把我们国家那么多年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料放起来供人研究。他看到中国兴批判,批判以后这些文章就见不着了,这种博物馆性质的馆藏,它虽然不说话,但它在那儿摆着,后人就可以根据这个能够发掘一些里边的内涵,能够更了解当时的社会发展形势。如果还保存在私人手里,再遇到文化大革命就全完了;如果在一个国家机构里就能得以保存。所以他特别希望有一个机构能把这些资料完整的、完好的保存下来。
现代文学馆的愿望,巴金已经实现了。现在对于他而言,还有一个,那就是修建“文革博物馆。”对此,巴金曾说:
我写文章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收到很多不认识的人来信,都赞成这个意见。我的一些朋友也都赞成。只要经过“文革大革命”的,没有人会不赞成。“文革”已经过去十年,“文革”造成的精神和物质的灾难,永远留在历史上,这是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我写了几篇文章专门谈这件事。
(十一)《隨想錄》是部什麽樣的書?
巴金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无疑是《随想录》。对巴金写作这部作品的背景,《巴金传记》是这样说的:
“《随想录》的那篇短短的‘总序’和谈影片《望乡》的第一篇,都是1978年12月1日写的,同时发表在同月17日《大公报•大公园》上。这个日子很有意思,因为第二天,12月18日,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第三次中央全会开幕。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冷静地估计了形势,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的新的方针和政策’。……三中全会的召开,巴金开始发表《随想录》,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表示全中国的人,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到一个普通的作家,都在深思同一个题目:过去的那一切灾难是怎样发生的,今后的路要怎样走?”
巴金的思考就写在这本《随想录》中。全书五集一百五十篇,包含了作者对历史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层思考。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披着‘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热。那么人兽转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的道路了”。他提出了一个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的主张:
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人们无从预测一座叫做“文革博物馆”的建筑物何年何月才会出现在地面上,但是,正如一些评论巴金的文章所指出的:“这部书,可以说就是一座袖珍的‘文革’博物馆。假如他年真的有那么一天建成了这博物馆,那么这书将是博物馆的最详尽的说明书。”
另外,巴金也和他的养子马绍民说过,他的所有作品中,他最满意的是《随想录》。
(十二)巴金故事•錢是用來買書的
巴金大部分的藏书,现在都已捐出去了。但在原先,汽车库、储藏室、阁楼上、楼道口、阳台前、厕所间、客厅里、卧房内……在巴金偌大的寓所内,曾经到处都是书。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他的藏书之多,在当代文人中,恐怕无人可比。
藏书多,自然在于书买得多。
巴金胞弟李济生曾谈起四哥爱书、买书的情况:
说到他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没有变。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有了稿费收入,个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买书。“一•二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去了他的住处,收藏的书也随之毁了。习惯已成,兴趣所在,书慢慢地又积累起来。去日本小住一年,就买了许多英日文版书带回来。有的名家作品他会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译本。住屋几乎全放满了书。解放后搬了家,房子宽敞了,书架、书橱也随之增多增大。书房内四壁皆书,客厅内也顺墙壁一溜立上4只大书橱,连走廊上、过道上也放有书橱。一句话,无处不是书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元银元。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蔬菜吃了。这两只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第2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巴金买书真的没商量。
在现存的300多封巴金与萧珊的通信中,有不少内容是关于寄钱买书的。1949年9月20日巴金书信萧珊:“昨天刚寄出一信,今早又收到你的信了。我还没有到开明去拿钱,过两天我会去拿的。其实我自己也不需要多少钱,不过来北平一趟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去送人,我自己也想买几本书。”从中可以看出,巴金这时在北京,准备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金已寄信嘱萧珊汇钱来,等不及又发信回去。
这是一封巴金写于1956年6月23日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
这次买书较少,已寄了几包回去,大概还有几包。
这次寄信的地点也是在北京。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去北京,没有一次不买书回来的。琉璃厂、王府井,都是巴金必去的地方。
(十三)巴金是怎麽走上文學之路的
巴金在怀念他大哥的那篇文章里,曾经很沉痛得说过这样一段话:
后来他居然帮助我和三哥(二叔也帮了一点忙,说句公平的话,二叔后来对待大哥和我们相当亲切)同路离开成都,以后又让我单独离开中国。他盼望我们几年以后学到-种专长就回到成都去“兴家立业”。但是我和三哥两个都违背了他的期望。我们一出川就没有回去过。尤其是我,不但不进工科大学,反而因为到法国的事情写过两三封信去跟他争论,以后更走了与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不仅他对我绝了望,而且成都的亲戚们还常常拿我来做坏子弟的榜样,叫年轻人不要学我。
1923年,巴金从家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之后的1927年1月,巴金登上了远赴巴黎的航船,那一年,他二十三岁。当时的愿望是到法国学一门可以“兴家立业”的技艺。
然而到法国后,在无政府主义发源地的法国,各种思想毫无疑问地冲击着巴金那颗年青的心,同时,国内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也触击着他的心灵。
那时的巴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感情无法宣泄,无处倾吐。巴黎圣母院的钟声让年青的巴金无法入眠,在接下来的一个个无眠的夜晚,巴金用笔开始宣泄他的爱与恨、悲哀与欢乐、受苦与同情、希望和挣扎。于是,便有了《灭亡》。再之后便有了《家》及“激流三部曲”,遂一发而不可收!
• 盛唐的诗人群体:王昌龄、崔颢和创造清刚劲健之美的诗人2007-08-16 18:03
• 盛唐的诗人群体:王维与创造静逸明秀之美的诗人2007-08-16 18:01
• 盛唐的诗人群体:高适、岑参和创造慷慨奇伟之美的诗人2007-08-16 17:59
• 苏东坡-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救药的文人”2007-08-16 17:57
• 怀念沈从文2007-08-16 17:53
• 激情孟子:中国传统文化的英雄还是祸端2007-08-16 17:44

关注一中官方微信

